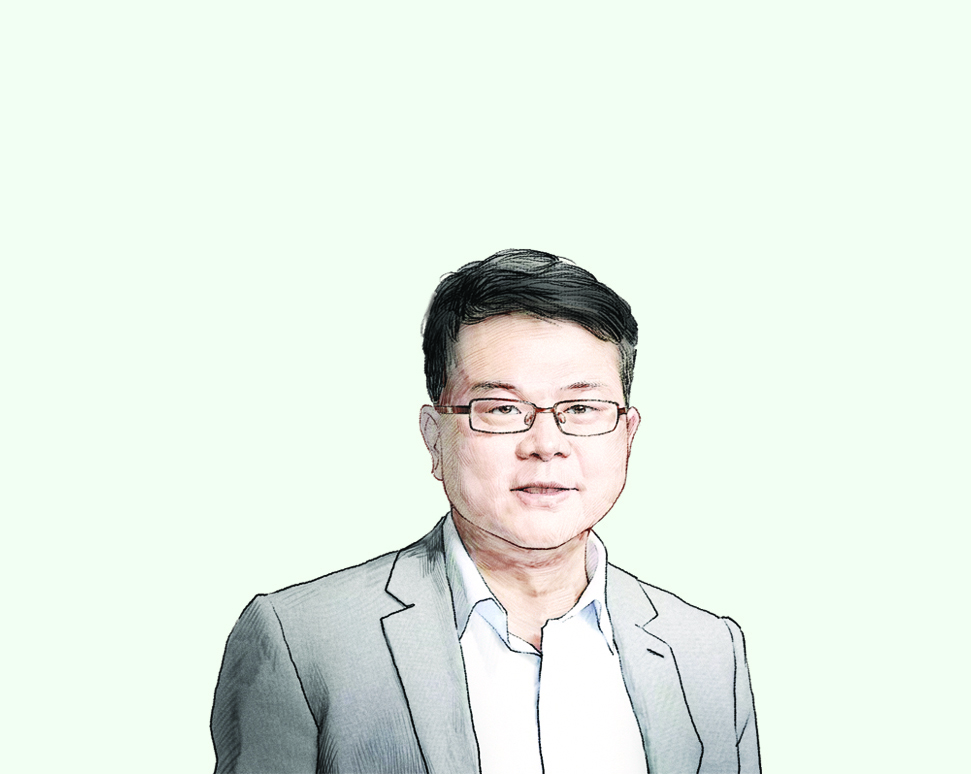
馮奎(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)
筆者在近期的“十五五”規劃調研中發現一個顯著動向:沿海省市正在將海洋從“背景圖”推向“主戰場”,比如廣東、浙江、福建等地多個城市紛紛將“海洋城市”寫入規劃藍圖。海洋大省廣東明確提出,推動廣州海洋創新發展之都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,支持珠海、汕頭、湛江等地建設各具特色的現代海洋城市。《湛江市特色型現代海洋城市發展規劃》《廣州市建設海洋創新發展之都規劃》等相繼出臺,為全國海洋城市建設提供了“廣東樣本”。
海洋城市這一新定位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方式的升級,更是對國家海洋強國戰略的積極響應,預示著中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有了更多“藍色”特征。
過去,盡管沿海城市一直處于對外開放的前沿,但其發展重心主要還是錨定陸域經濟,港口大多僅作為“出口通道”存在,海洋要素未能充分融入城市發展的核心邏輯。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來,建設海洋城市,核心是要將海洋從“輔助資源”提升為“核心增長極”,推動城市發展轉向“陸海統籌”。
這種轉變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戰略意義。我國管轄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,這是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所在。沿海地區已具備建設海洋城市的堅實基礎。以廣東為例,2024年海洋生產總值占GDP比重達14.1%,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近三分之一,海洋經濟已成為區域發展的“藍色引擎”。
建設現代海洋城市,打開了城市發展的新空間,提出了極具挑戰的新命題。從海洋城市規劃建設已有成效和經驗來看,最關鍵的是要以海洋新質生產力為核心驅動力。在前沿技術領域,要集中力量攻堅克難,比如依托海洋大學、實驗室等創新平臺,重點突破深海探測、海洋新能源、藍色碳匯等一長串的“硬科技”,讓科技成為城市向海洋延伸的“助推器”;在傳統產業升級方面,要大力推動數字化轉型,比如運用物聯網、大數據改造海洋漁業,打造“智慧海洋牧場”,讓傳統產業迸發新活力。
第二,我國發展海洋經濟,要與構建現代化城市體系深度結合。從全球經驗看,海洋強國的競爭本質是海洋城市群的競爭。比如日本東京灣城市群通過東京的金融航運、橫濱的高端制造、千葉的臨港產業協同,形成全球領先的海洋經濟集群;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,以紐約為核心、波士頓為科創支點、費城為制造基地,構建起“功能互補、聯動高效”的海洋城市網絡。我國的城市群、都市圈正在加速形成之中,建議在國家層面加強頂層設計,將“海洋城市帶建設”納入未來規劃,更加明確海洋經濟帶、海洋城市群、海洋都市圈、重點海洋城市群的功能定位。有關部委與省市之間要建立跨區域協調機制,在港口聯動、產業協同、生態共治等領域突破壁壘。在區域層面,要推動城市錯位發展。這方面,廣東的實踐頗具參考價值,比如廣州立足“海洋創新發展之都”,主攻海洋生物醫藥、海洋工程裝備研發;深圳以“全球海洋中心城市”為目標,強化國際航運、海洋金融功能;珠海、汕頭、湛江則分別依托生態優勢發展海洋旅游、圍繞臨港區位布局先進制造、立足資源稟賦做強現代漁業,有效避免了同質化競爭。
第三,應高度重視韌性城市建設以保障可持續發展。海洋城市直面臺風、風暴潮等自然風險,也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,韌性建設是“必答題”。在工程韌性上,要提升基礎設施抗災標準,比如修訂海岸防護工程規范,將臺風防御等級提升,確保重大設施安全;在經濟韌性上,應推動產業多元化,比如通過海洋旅游、海洋會展等內需型產業,對沖外貿波動影響;在生態韌性上,應加強海洋生態保護,比如推進紅樹林濕地修復、開展海灣綜合治理,守護海洋生態本底等等。
第四,以制度型開放提升全球競爭力。海洋城市天然具有開放屬性,需通過制度創新打開發展空間。下一步,在改革開放中勇立潮頭的頭部海洋城市,還需主動對接RCEP等國際規則,在海事仲裁、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擴大開放,同時深化與周邊海洋國家合作,比如與東南亞國家共建港口、聯合開展海洋環保項目,從“規則追隨者”向“規則參與者”轉變。
總之,從沿海城市到海洋城市的定位,不是地理范圍的簡單延伸,而是城市發展邏輯的深刻變革。在這個意義上,“十五五”掀開了海洋城市發展的新篇章。